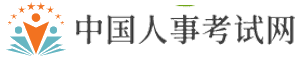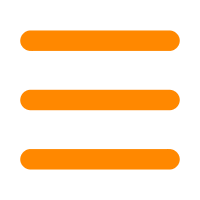摘 要 魅惑侦查,是刑事诉讼中一种特殊的侦查方法,其不当适用可能致使侦查陷阱。在美国判例法上,从对侦查陷阱的宽容态度到“陷阱之法理”再到“正当程序抗辩”,围绕魅惑侦查的合法性问题,演绎了规制侦查权的艰难经历,折射出侦查程序中关注人权保障的深层底蕴。由此得到启示,国内现在实践中魅惑侦查的无序状况也亟待法律规范。
关键字 魅惑侦查;侦查陷阱;陷阱抗辩;正当程序抗辩;法律规制
为了侦缉某些隐蔽性强的特殊案件,侦查职员总是设计某种诱导犯罪的条件或机会,待犯罪嫌疑人推行犯罪行为时,当场将它拘捕。这种运用诱导性方法进行刑事侦查的例子在实践中数见不鲜,侦查机关也将这种特殊的侦查方法当作出奇获胜之秘籍。问题是,假如被魅惑者原本乃清白之人,并无犯罪意图,他仅仅由于侦查职员推行的强烈魅惑而犯罪,侦查机关是不是有罗织圈套、陷人入罪的嫌疑?假如这种侦查方法是违法的,那样作为公民有没权利对之提出抗辩呢?
让大家看看最早对其进行理论研究的美国,可能能给大家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
美国于1910年FBI成立后,就开始将这种魅惑性方法运用于刑事侦查中,在特务活动频繁的二战期间尤甚。学界称之为Encouragement[1],可译为“刺激侦查”或“魅惑侦查”。它又因被魅惑者先前有无犯罪倾向而在理论上区别为机会提供型和犯意诱发型,后者就是本文要讨论的侦查陷阱(police entrapment)。对侦查陷阱的经典概念表述为,“侦查机关在本来并无犯罪倾向的无罪者心里植入犯罪进而对其惩罚”的办法来进行刑事侦查,因此陷阱抗辩应考察被告人有无犯罪的意图(intent)或倾向(prepsposition);而Roberts等少数法官则觉得“对于因政府自己的侦查行为鼓励(instigate)的犯罪,法院应该关闭对该罪进行审理的大门(即驳回起诉)”,从而将考察的焦点集中于政府的行为是不是在诱导犯罪。[5]这种分歧就为将来关于陷阱抗辩的主观说(Subjective approach)和客观说(Objective approach)的争论埋下了伏笔。
1958年的谢尔曼(Sherman)提供毒品案[6],是形成陷阱之法理(Law of Entrapment)的标志性案例。该案是因侦查机关的耳目在一家诊所治疗毒瘾时,遇见了也在那里治疗的谢尔曼,遂隐瞒我们的真实身份,多次需要他们提供毒品,谢尔曼再三推辞,但最后还是为他弄到了几包毒品,因此被逮捕。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援引了索勒斯一案中Warren法官的话,“决定陷阱抗辩是不是成立,需要在坠入陷阱的‘轻率的清白者’(unwary innocent)和‘轻率的犯罪者’(unwary criminal)之间划一条界线”,第三一定了索勒斯案中多数派的建议,撤消了地办法院对谢尔曼的有罪判决。同样地,参与该案审理的法官也有类似前案的内部之争,但仍然是主观说占了上风,从而使该案与索勒斯案一脉相承,确定了以考察被告人有无犯罪倾向作为侦查陷阱成立与否标准的“索勒斯——谢尔曼准则”(Sollors-Sherman Test),“陷阱之法理”基本形成。
二
尽管以“索勒斯——谢尔曼准则”为代表的主观标准说占据了美国司法界“陷阱之法理”的主导地位,但在学术界却引发了主观标准说与客观标准说的争鸣。前者以犯罪嫌疑人有无犯罪倾向为依据,后者以诱导行为本身性质为判断标准,孰是孰非,几十年来在美国可以说是争得不可开交。
反对主观说的人觉得,“不关注政府行为的正当性就不可能不同有犯意(prepsposed)和无犯意(nonpsposed)——这正是主观说忽视的原因”[7],因而具备非常大的片面性;并且因为主观犯意非常难判断,企图设定一个界限无异于制造了更大的不确定性,[8]因而不容易把握。虽然联邦司法系统和多数州采纳了主观说,但与之相对应的客观说仍然获得一席地位,获得了加利福尼亚等13州法院和多数学者的支持,并且被《模范刑法典》(Model Penal Code)所认同。[9]客观说早期以来自于国内法系的“魅惑者之法理”(Law of agent provocateur)为理论基础,后继联邦最高法院部分法官和一些学者的进步健全,得以对抗主观说。它强调陷阱之构成应考察魅惑侦查本身是不是具备诱发别人产生犯意的性质,而衡量的规范总是集中于侦查职员有无实行魅惑侦查的合理怀疑(reasonable suspicion)。他们提了两个原则[10]:(1)假如警察的行为引发了正常守法者的犯罪动机(motive)而不是普通罪犯意图,则侦查陷阱成立,比如,行为引起了某人处出于友情或同情犯罪而非因谋求个人利益或其他犯罪目的;(2)积极的(affirmative)警察行为假如一般能吸引一个正常的守法者参与犯罪,则同样构成侦查陷阱,比如警察行为包含:保证被告人所为不犯法或该犯罪不会被侦查,提供过高的报酬或类似的魅惑。
批评客观说的人指出,同样适合的魅惑行为,假如针对那些自制力弱的人,则非常可能是违法的;同样的过分的魅惑行为,假如针对意志力强的狡猾的犯罪,则可能毫无用途。[11]那样,完全抛开被告人的主观原因来判断侦查行为是不是构成陷阱,无疑也不可以防止片面性。
主观说和客观都不可以自圆其说,于是有人提出两者交流说。[12]他们觉得这种分类过分扩大了两者的差别,其实两者是相通的,理由有:第一,客观说所依据的可能性(likelihood)在非常的程度上依靠于诱导所针对的目的(target)只须警察将它注意力直接指向那些有犯意的人,构成侦查陷阱的风险客观来讲就非常小,魅惑行为就是允许的。在大部分状况中,只须被告人存在犯意,主观说和客观说都是允许进行魅惑侦查的。第二,大部分法院采纳客观说时都辅之以起因要件(causation requirement),此要件意味着被告人不只须说明诱导行为的非正当性,而且须说明魅惑行为导致他犯罪。假如此要件被严格使用,实质上主客观说之间的差别也就完全消失了。
在德劳瑞恩案中,主客观交流说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德劳瑞恩当时急切需要一千万USD来拯救其汽车公司,FBI的情报职员霍夫曼系德氏以前的邻居,向他透露了从事的毒品买卖,怂恿德氏卷入大宗的毒品买卖并借助其名下公司洗钱。德劳瑞恩因此遭到了逮捕,但结果被判无罪。尽管从陪审员事后发表的评论来看,他们好像采纳了客观标准说,但有人指出,该判决不但以否定FBI采取的侦查行为办法为基础,而且还基于政府不可以证实德劳瑞恩的犯罪之结论[13]。这事实上结合了主客观说之证明责任,给予主客观原因相同程度的关注,于是差别就无形中被模糊了。
三
1973年的拉塞尔案中[14],陷阱抗辩开始被上升到宪法的高度。
在该案中,侦查机关为了破获制造毒品的犯罪组织,向拉塞尔等被告人提供了一些制造毒品必需的材料和器材(并不是违禁品但入手困难),侦查职员以此为便利得以查询制毒现场并获得了毒品样品。当被告人借助这类材料和器材制造出毒品后,即以制造、贩卖毒品为由遭到逮捕和起诉。一审判决有罪,被告人不服,在二审时他援引了违法采集证据的排除法则,倡导侦查机关参与犯罪并在犯罪中发挥了很大用途,从而觉得对我们的起诉违反了法律的正当程序(due process of law)。但,联邦最高法院否定了被告人的原因,Stewart、Brennan和Marshall法官觉得,正当程序原则的确不允许执法机关为了使被告人被判有罪而采取违反刑事诉讼原则的过分行为,但本案中的侦查机关仅仅向被告人提供了并不是违禁的材料,并未违背违法采集证据法则,故被告人倡导的正当程序抗辩不成立。在本案中,法官讨论的焦点已不再局限于主观说和客观说的原有范围,而上升到政府的行为“是不是违背基本的正当程序原则(principles of due process)”、“是不是违背基本的公正和常见意义上的正义”的高度,[15]具备非同一般的意义。尽管该案及随后的汉普顿案(Hampton v.U.S.,1976)中,联邦最高法院都否定了被告人的宪法性(constitutional)抗辩,但并不意味着符合条件的正当程序抗辩不会被采纳,由于正当程序乃是支撑美国法律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果然,在1978年的托戈(Twigg)制造毒品案[16]中,第三巡回法院初次采纳了正当程序抗辩。这起案件是由侦查职员与友人托戈交往时,共谋制造毒品,之后又由侦查机关提供制造器材、材料和场合,当托戈与该侦查职员一同提炼出6磅毒品后,遭到了逮捕和起诉。审理该案的法官觉得,侦查机关的行为完全是以起诉虽有犯罪前科但过着平静生活的被告人为目的,“大家不可以容忍执法机关所推行的行为和对由此诱发的犯罪所作的起诉。”他们认同了被告人提出的正当程序抗辩,从宪法角度批评了国家执法机关诱使清白的公民犯罪的极端行为。但因为该判决是由第三巡回法院而非联邦最高法院所作,自然也遭致了一些非议,有些法院就遭讽正当程序抗辩是侦查陷阱的“私生子”,对此有学者立刻回话说,保护个人的宪法权利并不势必需要“大法官之足”(chancellor’s foot)先行。[17]
因为正当程序抗辩超越了传统的主客观之争,将政府行为纳入到合宪法性角度进行考虑,更严格地限制侦查陷阱的推行,因此,在魅惑侦查频繁发生的七八十年代之美国,其对于预防魅惑侦查的滥用,抑制侦查权力的恶性扩张,起到了积极有哪些用途。随后发生的震撼美国ABSCAM事件,使得对侦查陷阱进行法律规制遂成司法界与理论界的共识。以此为契机,美国司法部拟定了《关于秘密侦查的基准》,该基准在注意不与正当程序原则和“陷阱之法理”相抵触的首要条件下,明确规定了魅惑侦查的许可基准、申请程序的推行期间,从而达成了以法律规范的形式对魅惑侦查的规制。
四
丹宁勋爵曾言,“人身自由一定与社会安全相辅相成的。……每一社会均须有保护本身不受犯罪分子风险的方法。社会需要有权逮捕、搜查、监禁那些不法分子。只须这种权利运用适合,这类方法都是自由的守卫者。但这种权力也大概被滥用,而假如它让人滥用,那样任何暴政都要甘拜下风。”[18]作为侦查机关,维护社会安定,有效地打击犯罪是其职责所在,尤其是伴随社会进步,犯罪案件日益复杂化,已是一个不容忽略的现实。很多新型的犯罪(诸如贩毒、行贿、伪造货币、组织卖淫、互联网犯罪等等)以其高度的隐蔽性和高超的反侦查方法,对传统的侦查提出了巨大的挑战,社会治安形势不容乐观。魅惑侦查的产生正是适应了更有效打击犯罪的需要,并被实践证明为是一种很有效的侦查方法。因此,包含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在一定量上承认魅惑侦查的合法性。然而,正如本文所引案例时指出的,这种侦查带来的一个最大风险是可能致使诱惑犯罪,侵犯公民的权益。那样,在允许进行魅惑侦查的同时就应当防范“侦查陷阱”的形成。美国从对魅惑侦查的过于宽容到以“陷阱抗辩”限制,最后将之纳入宪法的“正当程序抗辩”,充分表明了刑事诉讼中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围绕着魅惑侦查权的行使和抑制,生动展示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透过美国规制魅惑侦查的演进轨迹,大家可以领会到刑事程序应具备的对于个人权利的深切关怀。
尽管国内刑事诉讼学界对于魅惑侦查理论还相当陌生,但不能否认在目前的犯罪侦查中却是存在魅惑侦查方法的。但,这种实践中通行的做法在法律上却找不到有关的依据。虽然公安部在1984年的《刑事特情工作细节》中曾对特情设制和证据采纳方面作过一些简单规定,但法律上对魅惑侦查的明确规制则依旧是一个空白。怎么样面对侦查陷阱——这是关系到达成侦查法治化的一个重大问题。“既然法律本身包括着产生专横权力的巨大危险,那样,法治的使命就是把法律中专横之恶和危险减少到最低的限度。”[19]基于此,笔者由美国关于规制魅惑侦查理论得到启示,简要提出如下什么时间规制国内魅惑侦查的建议:第一,魅惑侦查的适用范围应当是具备相当隐蔽性的无被害人案件,而且限于具备重大社会风险性的刑事案件,对政治犯罪则鉴于ABSCAM事件教训,不适合使用;第二,魅惑侦查对象应当针对那些“有合理依据或足够理由表明正在推行犯罪或有重大犯罪倾向的人”;第三,魅惑侦查的行为方法需要符适合度性原则,不能以侦查职员为主采取过分魅惑行为;最后,从程序控制上说,应当设定一个严格的审批监督程序,预防魅惑侦查的滥用。
面对侦查陷阱,大家也应当享有说“不”的权利。“程序的法治化,第一应当是侦查权力的法治化。”权力需要得以行使,但需要是合法地行使,侦查的合法界限在于侦查必要性与保障人权之间的衡平,魅惑侦查的底线在于不可以设置陷阱,不可以诱惑犯罪。在弘扬程序正义,达成法治的今天,大家是不是应当反省不足为奇的权力运作之隐患,是不是给予弱小的个人权利以更多的关注?这种考虑对于正在蓬勃发展进行的“严打”可能是一贴清凉剂。
美国规制魅惑侦查的法理评介
点击数:319 | 发布时间:2025-06-21 | 来源:www.25np.com
- THE END
声明:本站部分内容均来自互联网,如不慎侵害的您的权益,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
-
- 学习交流 -
-
欢迎加入中国考试人事网,与万千考友一起备考

- 成考路上不再孤单
专业院校
-
关注“考试直通车”
-
领取备考大礼包
-

点我咨询
返回顶部
Copyright©2018-2024 中国考试人事网(https://www.bzgdwl.com/)
All Rights Reserverd ICP备18037099号-1

-

中国考试人事网微博
-

中国考试人事网